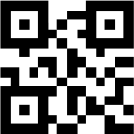1939年5月,日本对重庆的狂轰滥炸造成大量民众死伤流亡,中共在渝出版机构新华日报馆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加强舆论宣传,调整出版策略,谴责日寇暴行,呼吁团结抗战。
参与救亡活动
新华日报馆迁至重庆后,延续武汉时期将出版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式,在大轰炸时期参加了以青年节和劳动节等为主题的游行活动。1939年5月1日,报馆在董必武带领下,与重庆八办、生活书店及读书生活出版社等游行。游行队伍举着“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标语,由两路口行至储奇门,一路唱《国际歌》,喊“反对空袭,加强团结”口号。同时,《新华日报》印行劳动节特刊,登载董必武、凯丰、吴克坚、章汉夫等人文章,介绍国内外工人运动。报馆出动全体职工卖报,读者拿出1角、2角、5角、1元买报捐献,报馆也将一日经营所得63元3角献金抗战。
5月3日是济南惨案纪念日,报馆于当日下午在夫子池参加重庆报界会议,准备游行时日机便开始轰炸。5月4日,《新华日报》发布敌机狂炸重庆、市民伤亡极重和报馆房屋被炸坍的新闻,报馆职工坚持参加抗战游行,轰炸时才至中山公园防空洞躲避。
报馆办公建筑在轰炸中损毁严重:西三街2号的印刷部“被炸去大半,只剩下底层尚可勉强住人”;苍坪街69号的发行部亦被炸毁,艰难维持运营。
5月12日夜,日军轰炸江北,报馆职工疏散至磁器口,搭芦苇棚居住。在此情势下,报馆仍慰问同业,积极维系报界关系。如报馆致函中央社、西南日报社、新民报社,“以兄弟之情”“致慰问之敬礼”;致函记者学会总会,称“誓当追随同业先进”“以达到争取最后胜利”;慰问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惊闻联合版工友于忠、阮德成、陈英、陈义生四人,因公受伤,不胜悬念。敝报致以崇高之敬意和慰问”。报馆也收到同业和读者慰问。5月4日,《合川日报》称赞报馆“在危境中继续工作伟大精神”;13日,分销处吴同尘来函问候“报馆有无损失?工作同志又安全否?特此函慰问,希赐复,免焦念”;匿名青年发来慰问,“昨日我读了4日的报纸,知道苍坪街被炸,人员无伤亡。现特慰问……唯希望多为我辈青年指导”。国民党中央直属重庆市执行委员会亦致函报馆,“本市数日来迭遭敌机空袭,恣意授弹,损失惨重,文化机关亦多遭摧毁……继续加紧努力,坚持到底暴敌灭败指日可待”。
为救济民众,报馆直接参与抗战救灾活动。报馆依据中共中央组织各种劳动服务和社会服务的指示,在大轰炸后成立服务队。服务队驻西三街2号报馆营业部,由编辑、采访科等十几人组成,分为救援灾民、编印壁报两组。服务队救援灾民组在营业部门口设茶粥站服务灾民,开展现场救护、送医诊治、代写信件、慰问和采访被炸伤民众等工作;协助重庆市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发放救济款及救护在防空隧道中窒息不适的《大公报》编辑王芸生。采访科主任陆诒在《敌机狂炸了重庆》一文中建议加强各机关服务队秩序,设站地方应确有必要而不是拥挤在一处等。报馆服务队通过实际工作,在轰炸受难民众心中建立了正面形象。
加强舆论宣传
报馆不仅要面对轰炸带来的种种困难,还要应付国民党当局借机对舆论的钳制,以发出共产党的声音。国民政府借口大轰炸摧毁各报社房屋设备,使其无法出刊,强令《新华日报》等10家在渝报纸加入《重庆各报联合版》。中共中央意识到国民党力图通过《联合版》扼住《新华日报》喉咙,指示南方局与国民政府交涉,争取恢复单独出版;暂未恢复期间,充实《群众》周刊内容,尽量翻印和发行《新中华报》。周恩来致信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怆,说明《新华日报》为利团结同意参加《联合版》,一俟各报迁移有定所,《新华日报》即告复刊。在周恩来领导下,《新华日报》最终于1939年8月13日在化龙桥正式复刊。其间,报馆没有放弃在《联合版》发声,如在5月8日头版发布延安各界反对汪精卫投敌的大幅消息。
报馆服务队其中一组的任务是编印壁报。壁报组由姚黎民、徐光霄、黄铸夫、何耀光、王敬先5人组成,由姚黎民总负责,黄铸夫任美术编辑,负责编写、印刷、张贴、发行等事务。报馆编委会要求壁报组多为重庆民众说话,多反映当时遭受敌机轰炸的民众的抗战精神,同时揭露国民政府在赈灾中不负责任的行为。当时除白天空袭外,傍晚有“薄暮”空袭,月明时又有“夜袭”,壁报组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工作,一面要提早起来编印壁报,一面要挤在大隧道里躲避空袭。从5月9日至《新华日报》8月13日复刊,壁报存续三个多月,编印数十期。壁报版式为四开,样式和报头字体与《新华日报》相仿,只在下面横印“壁报”两个小字;开始是三日刊,后为双日刊,再到日刊;最初编本市消息,6月起加入社论,篇幅减成两大版,第一版是社论和国内外重要新闻,第二版反映陪都居民生活,有时为副刊;每期加一幅漫画或插图;出过几期特刊,如6月18日出纪念高尔基特刊,曾在国泰戏院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散发,刊载的汪精卫投敌消息引起过读者的特别注意;印行方式及发行量上,开始时一天手写十几份,6月2日起应读者要求改油印,发行量从200多份增至上千份,张贴于重庆街头巷尾;发行期间还应外省读者要求寄赠部分报纸。
《新华日报》壁报引起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注意。蒋介石在5月30日的日记中表示要“统一重庆市宣传与壁报”,国民政府中宣部不久便制定壁报检查条例,要求报馆将壁报送检,经涂抹盖章后才能张贴。重庆宪兵三团还秘密调查报馆服务队张贴壁报情况,记录《新华日报》壁报栏目有《说老实话》《上海通讯》《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并详列张贴地点有上陕西街莲花街口,下陕西街47号门首,新街口,大梁子,苍坪街,上新丰街浙江兴业银行门首,上新丰街42号聚兴诚银行门首,莲花街拔佳鞋店门首,劝工局街87、88号门首,武库街62、63号门首,龙王庙街90号门首,下大梁子怡园门首,夫子池临江门街口,中二路德国海通新闻社门首,关庙街62号及中山路67号左侧。这些地址遍布重庆城区的大街小巷,显示出报馆在重庆市内较为广泛地宣传了中共的方针政策。南方局青委领导的职业青年互助会等组织,也配合报馆,编绘和张贴抗战壁报。《新华日报》壁报版面灵活、形式生动,紧密结合轰炸时势、贴近民众生活、督促国民政府赈灾,发布了正式报刊在战时书报审查制度下无法登载的新闻,在大轰炸时期报馆出版物中起着特殊作用。
服务队使报馆门市部照常营业,以方便大量晚间前来阅读和购书的读者,并用持久抗战、抗战必胜的信念安抚轰炸后人们不安的内心。大轰炸后,报馆发行部数易其址,先后在苍坪街69号、西三街2号、化龙桥正街165号,始终不辍地为读者服务。
调整出版策略
大轰炸使后方民众与真实惨烈的战争紧密联系起来,加上轰炸后当局制定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新华日报馆调整了出版策略:一是印行大量辅助性的出版物以弥补《新华日报》在参加《联合版》时期宣传上的不足,二是将公开和秘密发行结合起来突破当局的新闻封锁,三是利用报馆发行网、战时书报供应所、生活书店等机构广为发行。周恩来分别会见编辑和印刷人员,指示新形势下报馆的工作任务。约见总编辑吴克坚和采访科主任陆诒,要报馆想方设法打破“沉闷空气”;到高峰寺看望印刷工人,作关于目前抗战形势的报告,指示报馆努力完成工作任务。周恩来还约见生活书店负责人邹韬奋,商议助力中共出版事业。
高峰寺位于磁器口,是红岩村大有农场女主人饶国模的房产。报馆最初为堆放武汉运来的存纸租赁此地,社长潘梓年后“呈报巴县县府备案”,注册为报馆印刷分所。大轰炸后,报馆正式将印刷部及部分编辑迁至高峰寺,成立装订房,调配纸张,以保证印刷所的运行。装订工人王禹斌回忆,高峰寺附近虽有电力充沛的兵工厂,但当局拒绝为报馆接线,自架专线又开销太大,因此没有电源。印刷所克服困难,使用油灯、蜡烛照明,手摇带动印刷机。当局给印刷厂和制本所施加压力,使他们不能接受报馆的承印和装订业务。于是,高峰寺印刷所建立装订房,添置简易设备,动员馆内力量装订、折书,为防止差错还加强检查。《新华日报》复刊后,装订房也搬到化龙桥。此后,高峰寺印刷所有林肖硖、陶师欧、苏吉成等12位工作人员,由林肖硖任所长,继续承担《群众》周刊和《列宁选集》等排字、浇版工作,再把纸型送到化龙桥印刷部付印、装订。
高峰寺印刷所印行《群众》周刊,负起党报任务;印行《新华日报》七七特刊和《新华日报》华北版,发布中共宣言;出版以《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为代表的“新群丛书”数十种;应共产国际要求,借国民政府与苏联关系缓和之机印刷《列宁选集》及苏共十八大相关书籍;翻印《解放》《共产党人》等杂志。此外,高峰寺印刷所还利用大轰炸后当局忙于应对以及地理位置偏僻不便审查的间隙秘密印刷大量宣传品。
大轰炸时期,面临巨大挑战的报馆仍通过各种措施保证发行。《新华日报》加入《联合版》前销量已达2.4万余份,加入《联合版》后,报纸社论改由《群众》刊登,订户亦改以《群众》寄递。除外地分馆及分销处外,报馆还有小龙坎发行站和沙坪坝代派处,报馆市内代售处尚存山王庙19号和丰号、磁器口周福旅社门口、上陕西街60号协益商店、一牌坊25号源森祥、段牌坊90号、龙王庙街62号等。为加强经营和联络同业,报馆还代售生活书店图书。生活书店重庆店总经理、中共秘密党员李济安亦通过书店发行网络发行报馆书刊,同时还秘密发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报馆积极与重庆地方党组织联系,利用相关机构加强发行。如职业青年互助会在化龙桥正街61号开设互助书店,秘密流传中共书刊。战时书报供应所在王爷石堡街五号院内设总部,在市内各处成立救亡图书室6所,由报馆筹募供应部分书刊。供应所还将这些书刊经战地文化服务社运送至五战区。
大轰炸期间,面对日寇暴行和国民党舆论封锁,新华日报馆采取灵活多变的应对措施,相当程度上扭转了这一时期中共宣传的不利局面,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创造了报馆出版发行事业的一个高峰,有力宣传了中共持久抗战、团结抗战思想。其与重庆地方党组织配合,为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发挥了作用。此外,报馆在轰炸时期的宣传工作和救亡活动,对新华报人来说是深入群众的实践锻炼,对扩大报馆社会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者:马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