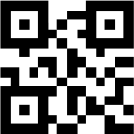重庆酉阳,是红二、六军团会师大会的举办地。从会师到成为红军的主力部队,红二、六军团在战斗中由不同地区、不同作战风格、不同管理习惯结为一支团结的队伍,是经受住考验的。贺龙曾说:“红二、六军团会师团结的很好,可以说是一些会师的模范。”
1934年10月24日,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在贵州印江木黄会合。27日,部队转移到酉阳南腰界召开会师大会。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正式宣布: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这一天起,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统一领导下,正式结为一个战斗组织。
会师后,由于两军历史传统、军事素质、作战方式等存在差异,新的问题开始出现。在此背景下,两支部队需要在战斗和发展中不断磨合。同时,红二、六军团还各自面临一些问题。贺龙说:“六军团需要休息,二军团希望会师后解决路线问题,党的领导问题。”受“肃反”扩大化影响,红二军团撤出洪湖根据地后,与中央失去联系,军心涣散,急需在组织上、政治上解决路线问题。红六军团作战78天,突出重围,部队损失严重,休养调整是最急切的问题。
虽然会师为两支部队创造了发展出路,但两支部队如何协调一致仍需在实际工作中逐步解决。通过政治、军事上的配合,以及组织架构上的调整,红二、六军团互相尊重、坚持团结,共同御敌并发展壮大,为创建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贯彻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
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仍控制着中革军委,导致许多指令不切实际。
1934年7月23日,为给中央红军探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训令,命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转移到湖南中部开辟新的根据地。红六军团很快意识到向湘中发展不切实际,容易遭到湘军堵截,于是决定向南转移。当部队转移到广西境内时,中革军委再次要求红六军团向邵阳地区开展游击战,与红三军在贵州东部会合后,再向湘西一带发展根据地。由于行动与训令不符,离开广西后,红六军团不断遭到中革军委批评。但由于中革军委的训令不切实际且自相矛盾,红六军团便不顾命令,继续在贵州作战,取得了新厂战斗胜利。
会师后,红二、六军团希望集中兵力统一行动,在湘西北开辟根据地,中革军委却要求两军分别行动,在湘西另寻根据地。1934年10月25日,任弼时、贺龙等向中革军委汇报敌情和两支部队的情况,认为目前“应集中行动”,由红二军团统一指挥,加强对黔东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乾城、松桃、凤凰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1]。然而,中革军委却先后于10月26日、29日电令两军,认为其合成一个单位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要求红六军团向湘西发展,红二军团向贵州方向行动。
两军领导人一面向中革军委陈述利弊,一面坚持集中兵力向湘西北发展。随后,两军占领酉阳县城,然后占领湖南永顺、桑植和大庸等地,并取得十万坪大捷。面对红二、六军团取得的胜利,中共中央书记处最终赞同其集中方式,于11月16日电令:成立湘鄂川黔省委和湘鄂川黔军区,两军团由军委直接指挥,但共同行动时,由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26日,朱德再次致电说明“二军团主力及六军团全部应集结一起”,两军“暂归贺、任统一指挥”。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放弃中央红军向湘西发展,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湘西根据地的计划。
湘鄂川黔根据地建设过程中,任弼时、王震、张子意等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领导发动土地革命,发出《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关于新区党的组织问题的决定》《分田工作大纲》《关于游击队中党的工作的指示》等。《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依靠贫农,巩固与中农的联盟”,“反对‘左’的侵犯中农利益与消灭富农的倾向”[2]。相关土地政策虽然没有彻底改变中央的“左”倾错误,但对保护中农、工商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两军共同努力下,以塔卧为中心的郭亮、永保、桑植、大庸四县建立起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四五十万群众投入革命建设中。
1935年11月,面对国民党军重兵压境,红二、六军团决定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在任弼时领导下,红二、六军团始终坚持正确政治路线,开展了大量政治工作,通过反复“政治动员、政治总结、政治检查”和“一次次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3],使将士们团结在一起,坚决执行中央交给两军团的任务。
跨过金沙江后,红二、六军团又面临新的问题。由于中央与两军的电文密码为张国焘掌握,两军领导人并不知道红一、四方面军的分歧和张国焘的分裂计划。早在1935年3月29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就发出电文询问,“最近国际和国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能甚明了,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活动是否孤立”,“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汇合,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望“在一二天内电告”。但张国焘的回电含糊其辞,只字未提林育英、洛甫等关于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到陕甘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主张。基于正确政治路线,任弼时、贺龙等洞察大局,没有被张国焘的手段迷惑,最终决定北上与中央会合,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7月5日,中革军委颁布命令成立红二方面军,彻底阻断了张国焘分化瓦解的企图,也使红二、六军团正式成为一个统一的战斗序列。朱德认为,“二方面军始终都是好的,听指挥的”,“因为二方面军忠于中央,迫使他(张国焘)取消了伪中央”。
创造共同战斗的军事胜利
湘鄂川黔根据地成立后,红二、六军团为保卫根据地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1935年1月,国民党军队集中11个师、4个旅,共81个团11万的兵力,分六路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围剿”。由于敌军强大,红二、六军团初期作战情况并不理想。2月11日,中革军委在电文中指出新的军事原则:“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须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电文还提出,在斗争确实不利时可以转移到川黔地区活动,这给了两军作战以极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基于此,红二、六军团在桑植附近的陈家河击溃敌一七二旅,次日又在桃子溪歼灭敌军,重新收复了桑植和大片根据地。
在新的军事原则指导下,红二、六军团剑指长江交通线,策应了中央红军转移,也回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板栗园战斗中,红二、六军团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伏击谢彬师部。芭蕉坨战斗中,击败陶广部10个团,打破了国民党军六路“围剿”计划。随后,两军主力先后占领石门、澧县、津市、临澧等地。一系列胜利扩大了根据地中心区域和游击范围,使根据地覆盖东起洞庭湖西岸,西至酉阳县境,南临沅陵边境,北达长江边鹤峰太平镇,西北至湖北咸丰忠堡和宣恩椒园,人口约百余万的广大区域。
长征途中,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2月创建了黔(西)大(定)毕(节)革命政权。黔大毕革命政权虽然仅存25天,但建立起8个区、95个乡村的苏维埃临时政权,扩红5000多人,壮大了革命队伍,迫使国民党再次集结重兵“围剿”。离开黔大毕后,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区辗转一个月,跨过了金沙江,使国民党的“围剿”计划落空。毛泽东称赞:“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执行融合互促的组织路线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两军在组织上作出新的任命,在保持原有组织框架的基础上,使两支部队融合在一起。
在政治工作上,决定由任弼时兼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原红三军政治委员关向应任红二军团副政治委员,原红六军团张子意、甘泗淇先后接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同时,任弼时、萧克、王震联名致电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认为夏曦执行“左”倾错误路线,取消党、团组织及红军中政治组织和苏维埃群众组织,导致原红三军政治工作陷入瘫痪,应撤销其原有职务。1934年11月1日,任弼时、王震、关向应、张子意联名致电周恩来,报告原红三军“肃反”扩大化情况及影响,建议以原红六军团政治部为红二军团政治部,红六军团另成立政治部,从红六军团调一批同志和四个总支书记,设法建立两个师的政治部,并迅速普遍建立党支部。随后,红二军团各级支部框架迅速建立起来。
在军事工作上,红二军团调一个团长到红六军团,红六军团调参谋长李达任红二军团参谋长,并调一部电台和相关报务人员到红二军团指挥部。贺龙和关向应还要求红六军团干部调入红二军团后,红二军团原有干部改为副手,或降为副职,或调出学习。如红六军团的方理明到红二军团第四师当政委,原师政委朱绍田则调任第十团政委;红六军团的袁任远到红二军团第六师当政委,原政委廖汉生则改任副政委;红六军团的冼恒汉到红二军团第十六团当政委,原政委汤成功调出学习。通过组织上的交流,两支部队在政治、军事上不断协调。
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建立后,两军的结合更加紧密。1934年11月,湘鄂川黔省委成立,任弼时任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为委员。同时,湘鄂川黔军区成立,司令员及政委由贺龙、任弼时兼任。由此,红二、六军团一致行动得到了中央肯定,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结合。中央书记处在11月16日的电文中指出,要“团结一致,努力为创立湘川黔边新的苏区的任务而斗争”。湘鄂川黔省委成立后,经决定,任弼时、王震和张子意率红六军团第四十九、第五十三团和红二军团第十六团留守后方,开展根据地建设,贺龙、关向应和萧克率红二军团主力和红六军团第五十一团开展军事斗争。
1935年1月27日,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在大庸召开。任弼时总结了红二军团工作上的转变和弱点,指出党的工作在红军中的重要性,并以实事求是的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指出夏曦过去错误的原因。红二、六军团在组织上的配合与交流,使两支部队成为一个团结的战斗组织。
互相尊重,坚持团结
会师前,贺龙得知红六军团进入贵州后,立刻派出队伍寻找并做好接应准备。当时,红三军的处境也十分艰难,如果为寻找红六军团深入敌后,很可能被敌乘虚而入。但贺龙认为红六军团更需要帮助,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做好接应。
会师时,两军将士都十分激动。在南腰界召开的会师大会上,贺龙称任弼时为“任代表”,并为红六军团将士安排食宿,让其休整体力,准备战斗。任弼时向红六军团将士介绍贺龙:“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红三军的军长贺龙同志!”部队整编后,尽管红二军团也很困难,但仍全力帮助红六军团。抽出一批骡马为其托运辎重,收割茅草打草鞋和铺盖,以及送粮等。贺龙回忆说:“我和弼时同志开始见面并成为亲密的战友……由于两个军团的会合,特别是弼时同志的到来,给我们以无限的兴奋和力量。”[4]萧克谈道:“我在任弼时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几年,以后又听别的同志称道他的领导作风,我感到善于团结干部一道工作,是任弼时同志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到湘赣苏区后,是苏区的领导和团结的核心;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又成为两个军团领导和团结的核心。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来自两个不同的苏区,会师以后,能够成为团结的模范,正如贺龙同志所说‘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一方面当然是在敌人追剿的情况下,团结战斗是两支队伍的共同要求,但另一方面,和中央代表任弼时及红二军团领导人贺龙、关向应等同志互相尊重、善于团结有很重要的关系。”
出于团结考虑,贺龙在工作中对红二军团将士十分严厉,对红六军团将士则充分包容。一次战斗中,红六军团出身的方理明、杨秀山(后调至红二军团工作)受伤,贺龙主动慰问,给予红六军团战士极大鼓舞。此外,原属红六军团的余秋里和原属红三军的贺炳炎因换军装问题产生矛盾,贺炳炎找到老首长贺龙诉苦。贺龙却对其进行批评,使贺炳炎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此后,从长征到抗战,余秋里与贺炳炎一直合作得很好。
回顾红二、六军团的发展史,廖汉生认为两支部队的成功在于两军性质相同、目标一致,在于两军首长和战士讲团结、顾大局;坚持正确政策作为队伍团结的根本,为队伍指明了前进道路;尊重与合作作为队伍团结的保证,为队伍不断发展提供了精神指引。红二、六军团的团结精神,始终值得现代人继承和发扬。
作者 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