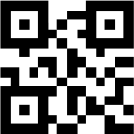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它营造了中国战略大后方,改善了全国生产力布局,为21世纪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工业基础。
重庆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
1964年,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如何防御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问题。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
根据毛泽东系列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的意见,9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正式宣布:“三线建设的目标,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办法,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初步设想,一是“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材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器设备的基地”。二是“用五年到六年的时间,把酒泉钢铁厂建设起来,依靠这个原材料基地,在西北地区初步建设起一个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必要机械设备的基地”。三是“用七年到八年时间,依靠攀枝花原材料基地,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全的包括冶金、机械、化工、燃料等主要工业部门的基地”。1965年2月,中共中央对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的报告作出指示,强调“应当从准备打仗出发,重庆地区常规兵器工业以及为此服务的其他工业项目都必须抓紧。要全力以赴协同作战,力争三年或多一些时间陆续完成”。
在三线建设酝酿和决策阶段,重庆一直受到中共中央关注。1964年夏,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即在驻地接见了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他说:“中央决定要搞三线建设,你们重庆是一个重点,有什么困难?”鲁大东说:“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个战略决策,重庆的工业有点基础,但交通有点问题,运力不足。”毛泽东幽默地说:“运输有问题,把我的车开去吧。”毛泽东还询问了重庆工业和军工生产情况。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和中央的战略决策很快得到贯彻落实,三线建设迅速展开。
同年11月,李富春及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等一行32人来重庆视察,研究部署有关三线建设的工作。
1965年4月16日,来渝视察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以及中共中央西南局负责人李井泉、程子华,在潘家坪招待所听取了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朱光关于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基地建设和战备增产工作的汇报。中央领导同志指示要抢时间,加快建设后方基地,尽早准备以应战时急需。
9月24日,周恩来飞抵重庆,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访问。在潘家坪招待所,他专门抽出时间部署白市驿机场扩建为二级机场的有关工作。25日,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乘船去武汉,特意通知鲁大东登船作三线建设情况汇报。当鲁大东汇报到三线选点布局原则时,周恩来说,大三线建设的方针仍是“靠山、分散、隐蔽”,但是分散中也要注意生产流程、生产工艺的合理性。生活区与生产区离远一点有好处,但也要注意不能搞得太分散。对于选择的迁建项目一定要配套,一种产品在三线选点布局要形成生产能力,成套生产,不能缺了胳膊少了腿,打起仗来用不上。
11月中旬,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薄一波、李井泉等陪同下,到重庆视察军工企业。他先后参观了建设、重钢、长安等厂,并在住所召集了五次会议,主要听取有关三线工作的汇报。他还就重庆南线(长江以南)的100毫米高射炮生产基地、北线(长江以北)的光学仪器和核工业基地、长江沿线的造船基地及配套的研究所等重大事项进行了论证部署。
重庆三线建设的总体布局
三线建设中,重庆常规兵器基地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增加大口径火炮及炮弹生产,新建生产厂点,生产主要用于地面压制的榴弹炮、加农炮、迫击炮和大口径高射炮及相应炮弹;增加新型武器品种生产,如各种战术导弹的战斗部;对重庆主城老厂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和改造,加强防空能力;疏散重庆主城老厂一部分生产力量。新建兵工企业主要布置在重庆周边山地丘陵中。
当年,重庆在南线新建了一系列生产大口径地面压制火炮(不包括迫击炮)及大口径高射炮的企业,主要有147、157、257、5007、5017、5027、5037、5047、5057、5067等厂;在北面及西北面地区布置了308、338、348、398、598、268等厂,主要生产炮瞄器具及光学产品、大口径炮弹及战术导弹战斗部。此外,还布置了一个迫击炮专业厂(167厂)。
重庆兵工原有七大厂,即长安机器厂(456厂)、望江机器厂(497厂)、空气压缩机厂(256厂)、建设机床厂(296厂)、嘉陵机器厂(451厂)、江陵机器厂(152厂)、长江电工厂(791厂)。三线建设时期,重庆兵工厂按照对空防御要求,对洞窟进行了扩建加固。在重庆主城新建的兵工企业有虎溪电机厂(5019厂)和七一仪表厂(5077厂),前者利用已撤销建制的重庆炮兵学校校址建造,后者利用当时停办的重庆工业学院校址建造。
1966年9月1日,根据国家计委、国防工办批复,重庆地区开始100毫米高射炮各厂基本建设。1967年初土建工程动工,1972年底各厂基本建设工程结束。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建成。新建兵工企业34个,在重庆市区改建2个,新建研究所2个,单位总数达到48个。这些兵工企业能够研制和配套生产40多种比较先进的陆海空常规武器、坦克与装甲车辆、特种装备,以及配套的光学仪器、弹药、火工产品。
在长江上游地区建设船舶工业基地,也是三线建设的重要部署。1965年起,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星负责组织踏勘,在下起万县上至永川、江津的沿江地带,按照靠山、近水、扎大营的建设思路和船、机、仪三大系统,分片布局了船舶工业及其配套企业,共计22个单位。
在涪陵至重庆沿江地带布局了涪陵川东造船厂(432厂)、重庆造船厂(429厂)和卫东造船厂(未建成投产即转交地方改建为渝州造纸厂)。在永川、江津建成了完整的船舶动力机器制造基地,主机企业为国营长江柴油机厂(405厂),配套企业有红江机械厂(465厂)、跃进机械厂(466厂)、永川液压件厂(462厂)等。万县船用仪表基地主要企业有永平机械厂(452厂)、江陵仪器厂(454厂)、长平机械厂(455厂)、江云机械厂(457厂)、武江机械厂(487厂)等。该仪表基地对海军建设贡献很大。南极科学考察船上的平台罗经、太平洋洲际导弹发射的导航定位系统等都由这里的工厂生产。后来,452、454、455、457、487五厂合并搬迁到主城区,组建为华渝电气仪表总厂(453厂)。
当时,中央在重庆地区还安排布置了其他国防工业单位,涉及核工业、航天工业、军事电子工业等,如三线建设进洞的原子能反应堆及化学后处理工程(代号816)、航天地面控制设备生产厂巴山仪器厂(289厂)等。中央还对迁渝的冶金工业企业、机械工业企业、仪器仪表工业企业、化学工业企业等进行了扩建。
这一时期,重庆地区能源基础设施得到很大加强。煤炭工业建设的重点是松藻矿区和天府矿区,先后建成打通一矿、打通二矿、刘家沟矿、杨柳坝矿等,新增设计生产能力近400万吨。电力工业建设重点为电源点和送出工程。重庆电厂在1967年6月和1969年6月先后各建成投产1台5万千瓦机组,总装机容量达到29.6万千瓦。1975年5月,川渝电网第一条220千伏输电线路豆渝线建成投产,川西水电开始东输重庆。
同时,交通建设也实现快速发展。1965年10月,川黔铁路正式通车。1970年2月,襄渝铁路开工,1978年5月全线竣工,重庆去往北京不再绕行成都。港口码头方面,九龙坡重件码头增设了起重能力180吨的作业线。重庆港拥有机械化码头13座,最大停泊能力达到3000吨,年通过能力达到632万吨。
重庆三线建设重大工业项目
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重庆安排了一批重大工业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建成投产后,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南铝“四大设备”制造与安装投产
三线建设期间,在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封锁、中苏关系破裂的背景下,新中国装备了“九大设备”。其中,3万吨模锻水压机、1.25万吨卧式挤压机、辊宽2800毫米热轧铝板轧机和辊宽2800毫米冷轧铝板轧机“四大设备”就装备在西南铝加工厂。
西南铝两套水压机共有设备298种、460台(套),总重量2.48万吨,主要用于飞机、导弹的翼梁、壁板、型材、鼻锥的锻造和挤压成材。两套铝板轧机共有设备221种、303台(套),总重量超万吨,用于轧制飞机、导弹所需的宽大铝板。时任冶金部副部长高扬文称,西南铝为“冶金战线三线建设第二个有重要意义的项目”。其建设投产“标志着中国铝加工业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这个厂和攀枝花钢铁厂一样,证明中国人民具有雄心壮志,不管有多大困难,看准了、下决心要办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办成”。
西南铝四大设备属于国宝级设备,过去不宣传、不开放参观,世界上拥有这类设备的国家只有少数几个。改革开放后,美、日、德等国专家前来参观,对中国20世纪60年代研制出这样的设备无不表示惊讶和赞佩。西南铝3万吨水压机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承接美国波音飞机公司大型锻件加工业务,其中钛合金起落架可以算是世界上要求最严格的锻件。
重庆重型越野汽车生产基地的建设
20世纪60年代,我国生产的重炮、导弹陆续装备部队,但用于牵引的重型越野汽车却无法生产。国家拟在西南地区建设一个重型军用越野汽车生产基地,由四川汽车制造厂、重庆汽车发动机厂、綦江齿轮厂、重庆汽车配件制造厂、重庆红岩汽车钢板弹簧厂、重庆油泵油嘴厂和重庆重型汽车研究所组成,简称“六厂一所”。
1964年初,中法建交。根据周恩来的安排,第一机械工业部组织重型汽车考察团到法国贝利埃公司,谈判引进他们的重型越野汽车技术。经过艰苦谈判,最终以860万美元引进了贝利埃公司GBU15等四种车型及相关的三个发动机产品制造技术。同时,用610万美元引进西欧六国工艺设备78台(套)用于该项目。
重庆重型越野汽车生产基地建设采用新厂建设和老厂改造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大足新建汽车制造厂负责重型汽车底盘、钣金件总成制造以及总装,其余各老厂经过改造扩建以后,生产发动机、变速箱等总成和部件配件。
1965年,国家从济南汽车厂、长春汽车厂等单位抽调优秀员工赴川建厂,并组建重型汽车研究所。1975年,以四川汽车制造厂为主,组成四川重型汽车制造公司。公司成立后,推动了生产发展。
1979年,重型越野汽车产量达到500辆。四川汽车制造厂生产的重型越野车红岩CQ261自投产后便成为我军主要的重炮牵引车、122毫米火箭炮底盘、地地导弹牵引车。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CQ261凭借出色的越野性能,在崎岖山路畅行无阻,立下赫赫战功,被誉为“红岩神炮”。
鞍钢第二中板厂搬迁
1964年9月,国家确定鞍钢第二中板厂为首批内迁三线的重点项目之一。该厂以重钢生产的扁锭为原料,生产6-40毫米中厚板,年产能力20万吨,其中产军工合金板2万吨。主要生产设备除来自鞍钢搬迁,还新增后部工序以及相应的铁路、公路、供排水、供电、天然气输送等设施。
鞍钢负责中板厂设备拆卸和大修工作。从1965年2月10日开始,鞍钢职工仅用67天就完成了半年工作量,对390个台组的机电设备进行了拆卸、清洗、修理、调试、刷漆、编号,并备足备品备件。他们将7000余吨设备及备品备件分装2200箱,用524节车厢载送到重庆刘家坝。随设备内迁重庆的职工257名,其中干部和技术人员50人,其余均为熟练的技术工人。
鞍钢在这次中板厂内迁工作中,体现了高风格、高质量、高速度。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后来回忆:“鞍钢发扬了很高的风格,在迁厂时不仅为该厂配备了较强的班子,选拔了政治条件好、技术等级高的技术工人,而且对迁出的67个机组和390台电机设备进行了全面检修,检查质量都达到了技术标准。在运输中,7000多吨设备全部完好无损。”
1965年12月14日,刘家坝中板厂竣工投产,轧出第一块钢板。该厂正式定名为重庆钢铁公司第五钢铁厂。
四川维尼纶厂——国内最大的天然气化工企业
1973年初,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从国外引进43亿美元成套工业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其中,四川维尼纶厂是当时成套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建设的全国四大化纤项目之一。
四川维尼纶厂位于重庆市长江下游北岸,是我国最大的以天然气为主要原料生产化工、化纤产品的大型联合企业,也是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综合性化工企业。该厂于1974年8月动工兴建,1979年12月全程投料试生产成功,1983年被国家正式验收竣工投产。全厂设有化工厂、化工二厂、化纤厂、化纤二厂、热电厂、机械厂六个生产厂,主要装置分别从法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家成套引进,达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
该厂设计规模为年产维尼纶短纤4.2万吨、维尼纶牵切纱0.3万吨、甲醇9.5万吨等,投资概算10.43亿元,是三线建设最大的工业项目之一。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厂生产的维尼纶占全国产量四分之一,聚乙烯醇占全国产量三分之一,甲醇占全国产量八分之一,产品质量全国领先。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四川维尼纶厂多次扩建,还与英国BP公司合资建设了中国最大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醋酸生产项目。
重庆三线建设调整改造
三线建设时期,大批企事业单位迁入山区后,由于有的地方地质灾害严重、规划投资综合平衡不够,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这些都对三线企业的原材料供应、生产经营以及职工生活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我国发展战略调整,原来为应对战争爆发而建立起来的三线企业,遭遇任务锐减、生产线闲置、企业亏损严重、职工队伍不稳等困难,大批三线企业难以为继。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重庆三线建设调整工作于1984年逐步展开,三线建设工业企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纳入全市经济发展中进行通盘考虑。在长达三个五年计划的调迁过程中,国家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调整方式。一是把性质相同、工艺相近的厂、所合并调迁。如兵器54所和62所合并迁建为兵器59所;将位于重庆南部山区的9家大中型军工企业集中调迁至巴南区鱼洞镇,合并组建成重庆大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二是将调迁与技术改造、引进外资和技术相结合。重庆市43家调迁企业实施较大的技改项目50个,投入技改资金12亿元,开发新产品423件,引进外资9760万美元,办合资企业20多家。这些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与调整前相比明显好转。三是老厂不动,将科研机构和民品生产线调迁。如红宇机械厂的军品生产线不动,将民品生产线调出山区,军品、民品生产实现了较快发展;一坪化工厂是厂所合一的单位,把研究所迁入城区,另择地新建年产5万吨的高级润滑油生产企业。四是就地调整改造。如建峰化工总厂(816厂)原是国家重点投资的核工业企业,1993年上马了第一条化肥生产线,使企业摆脱了困境。五是企业调整与三峡库区淹没企业搬迁相结合。如重庆合成制药厂既是三线企业,又是三峡库区淹没搬迁企业,在调整中建设了比原来规模更大的新厂,形成了既生产原料药又进行深加工的新局面。
调整改造期间,原散布在偏远山区的40多家国防工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先后迁入重庆市区和郊区,使重庆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四大工业片区。一是南岸区南坪电子仪器仪表工业区(338、789、759厂和电子24、26、44所调迁于此),二是巴南区鱼洞汽车及重型机械加工工业区(南线布点的9个兵工厂调迁于此),三是江北区冉家坝精密机械电气仪表工业区(万县的452、454、455、457、487、489厂调迁于此),四是九龙坡区石桥铺科研区(兵器59所、航天机电设计院、机械部第三设计院、中石化润滑油研究院、重型汽车研究所等调迁于此)。这些企事业单位的调整迁建,不但促进了一批工业新区和企业集群的兴起,更为20世纪90年代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及21世纪初重庆两江新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重庆市列入国家计划的三线调整项目共45个,批准投资49亿元,到2002年实际完成投资54亿元,完成了国家批准的调迁任务。重庆市三线调迁项目大约占同期全国三线调迁项目的五分之一,完成投资占四分之一,调迁项目及完成投资在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各省中位居前列。经过调整改造,截至2015年,重庆有军工企事业单位42家,分别隶属于兵器装备、兵器工业、船舶重工、航天科工、航天科技、中电科技六大军工集团,资产总额2337亿元,职工14.8万人。长安集团、中船重工重庆公司等一批军民结合的大型企业集团强势崛起,汽车、风电设备生产跃居全国前列,军事电子、自动控制等迅速向民用转移,加快了重庆传统工业的更新换代。
重庆军工企业在调整改造中实现了“军民结合”,“军民两用技术”扩散初显成效,“民为军用”取得进展。如今,重庆在军民融合道路上积极探索、大有可为。
作者 马述林